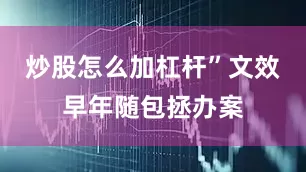
此文前,诚邀您点击一下“关注”按钮,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,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~
文|避寒
编辑|避寒
文|避寒
编辑|避寒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七月初三未曦,汴梁鼓楼依旧昏黄,忽有二十一口黑漆棺材自七座城门同时抬出,哀乐不响,旌幡不动。
街头只传“包青天大去”,却无人知真柩所在,九百年后,谜底才在江淮一隅显出轮廓。
展开剩余89%临终嘱托:二十一副棺材的生死局
包拯六十四岁,病在开封相国寺北廊官舍,五月,乌云压城,暑气闷重,他还照例把奏牍摊在膝前。
奏牍上列着人名:张方平、庞籍、王拱辰……这些曾被弹章直指的权要,如今静观对手衰弱,他们等一个时机,或是诛谤,或是辱尸。
北疆辽骑年年南探,西夏屯兵灵州,战报频上枢密院,包拯心中衡量:一旦边城失守,敌骑直逼汴梁,驸马、贵戚难保祖坟,他这座素冢更是囊中之物。
再算家仆寥寥,子嗣无显官,吏部的告身纸上,他封至枢密副使,却拿不出护坟之力。
开封流言不止,有说权臣要“报一箭之仇”,也有说契丹早设线人盯包府墓地,朝中有人劝他迁葬他乡,躲避后患,他没理,夜里反而独自看账册,查开封府从前流放、处决、赈灾、救济的细账。
有人问他为何事烦心,他只说一句:“我去后,不要让百姓再为我劳神。”
六月初,病势陡转,包拯把女婿文效召到榻前,夜色淹没了油灯,蜡泪落在几案,他只留五句话:
“备棺二十一,分七门齐出,真柩掩日落桑垄,代代唇守,不许纸透风。”
“备棺二十一,分七门齐出,真柩掩日落桑垄,代代唇守,不许纸透风。”
文效早年随包拯办案,胆硬心细,他即刻遣人南下寿春,搜购上等楠木,选干木匠密造棺罩。
契书只写“义木济人”,不露亡者名号,棺成二十一具,外罩二十一匝,每具厚寸半,榫卯紧密,可隔水蛀虫。
除此之外,还秘密召来包府老仆七人,各自记住一段路、一组号码,最终藏棺位置只有文效与两名忠仆知晓。他们在包拯榻前跪了整整一夜,未哭,不语,只记路线,不敢遗忘半字。
七月初一,包拯气衰声微,仍撑身批殿前司讼狱,纸未干,他忽抬眼看门外树影,道一句“留清白”便阖目。
家人未及哭,文效已点灯开箱,分派七组抬夫,各收一副真棺、两副空棺,连夜潜伏城隅。
出殡奇观:七门同出的疑冢计
七月初三寅时,开封鼓楼尚未击早更,城门军士听到内城窄巷忽起脚步杂音,暗号齐发,七门同时开启。
东华门外,挑菜贩刚放下担子,看见三副黑棺无声而去,有人惊呼:“包家族灭?”西水门畔,河泊所钓徒见棺影映水,心底发寒,谣言炸裂,“包公弹章惹祸”“皇命诛九族”,市井瞬间乱。
城南酒肆掌柜听说“包家送出二十一棺”,吓得没敢开门,开封府内衙档房也一夜未歇,怕有人趁乱造假文书、传讹生事。
隔日,数十家店铺挂白,百姓上街打探虚实,无人知真柩去向,谣言越来越大。
棺队出门即散,三口循汴洛驿道,三口沿黄河堤柳,三口越陇海古渡……每路领队持木牌,上墨书“包氏先人”,不示官阶,不插家纹。
真柩蒙粗麻布,置骑从中央,由文效亲护,队伍昼伏夜行,过睢水、渡淝河,黎明抵庐州东乡桑垄。
桑垄前,早备好石灰、细砂、生土,抬夫挖坑三丈,垫碎石,再铺石灰、木炭、朱砂,真棺下葬后覆沙覆土,又撒麦粒,夜风一吹,地面只余薄薄麦茬,毫无新坟痕迹。
一盏孤灯照得文效面色惨白,他用铁锹平整最后一抔土,低声念“清白入土”。
开封府东角门贴出黄榜:包孝肃相国丧仪从简,家属辞谢奠礼,谢绝公祭,榜后附一行小字:“余棺赠寒士,无限取用”。
乞儿、穷户拥向包府仓廒,把二十副空棺拆成门板、床板、木箱,木香散入市井,人们明白:包公死后仍在济困。
更有传言,说“棺中有一金匾,藏着罪臣名单”,甚至有人扬言要买空棺刨开查找,但当真有人拆了一具空棺,却只见粗麻席一卷,内嵌白骨残片,全无一文,才止了流言。
城内风声稍缓,有人探听真柩所在,撞见府尹手书告示:“探坟者杖六十。”告示贴了一夜,第二日无半人敢问。
仁宗默许,没有颁下一纸谕令;权贵噤声,也无人出手阻拦,疑冢计已成,真与假在烟尘里调位,留下漫长暗影。
盗墓禁忌:包拯墓为何无人敢动?
从宋至清,江淮一带的盗墓贼不下百拨,惟独对包拯墓群始终避让。这并非因其陪葬丰厚,反是因为“实在没值钱的东西”,真因,在行话里只三个字“不敢碰”。
南宋初年,战乱不断,百姓南迁,盗墓之风也由中原蔓延至淮南,开州、庐州、舒州一线成盗掘高发地,尤其古墓多的河套村、梅山岗、铜井街。
但凡传出是“达官富户”埋骨之地,盗贼总能摸出一条道来,唯独包家冢,一次都没被撬动。
淮西土匪头目贺仁五晚年口述过一段往事:年轻时曾夜探桑垄,带了两锹三镐,刚翻两锄,脚下沙土陷落,他人没摔,心先凉,有人说听见地下有铜器互撞的声音,扔了工具就跑。
他在赌坊里跪着发誓:包孝肃墓,生死不碰。此后成了规矩,盗墓贼自己立了一道线,义冢不撬。
所谓“义冢”,是指清官、义士、忠烈之后,家无厚产、冢无金玉,却有名节。
包拯在开封治案六年,平冤沉、断赃案,凡百姓打赢官司者,都会在衣襟上绣一个“公”字,以示纪念,等他卒后,这层敬畏深入街巷。
据明代笔记《庐州遗事》记载:元末群盗扰庐州,一伙人夜宿桑垄边,次日全队染病,死者三人。
自那起,“包冢有神”之说传遍淮右,村里老人守着家谱口述:包家祖训“不贪赃滥者始得归祖坟”,下葬者须由长房验身,非清白不得葬入。
更难得的是,地方也配合,明洪武年间,开封重修包公祠,奏章中特别附带一句:“不可迁其冢。”意思很清楚,哪怕修祠做官样文章,也不许乱动地下半寸土。
清代《合肥县志》里亦记载:“包公冢在大兴集东北,不表其坟,垄植桑麦。”
盗墓不是不识真伪,而是敬而远之,一块没人立碑的麦地,一代代村人轮换种地,却没人敢翻土盖房,风水不是术数,而是人心。
九百年后真相:1973年考古揭秘
1973年,合肥大兴集扩建钢厂,推土机深挖厂房基础,突然铲起石板一角,石上满是朱砂痕迹,还有墨线圈,当地文物部门赶到现场,立即封锁工地,展开救掘。
探方打开三天,露出墓道,两侧墓砖三层,夹青灰缝,下探四米,见一砖券式墓室,北首甬道刻小篆七字:“宋孝肃包公之墓”。
石函内置木炭、石灰、朱砂三重套封,中部放有破损铜镜一面,墓志一块,竹简三枝。
竹简为后代所留,仅八字:“犯赃滥者,勿入祖冢。”落款为“包继庚”,正是包拯长子。
铜镜无花纹,背后有一行隶书“警己”,无银饰、无玉器、无金铠,墓志则列明其生卒、官职、谥号“孝肃”,内容与《宋史·包拯传》基本吻合。
最特殊的是尸骸已朽,骨灰中检测出高浓度汞元素,正是朱砂长期防腐所致。
从墓中物品判断:无任何随葬奢物,冢内地面平整,未见棺床痕迹,推测即为“草草掩埋”,更印证出殡二十一棺、“真柩藏麦垄”的记载并非妄谈。
文物部门未大肆修复,仅建围栏保护原址,并在附近设纪念标牌,此后包拯墓正式对外开放,不以雕梁画栋取胜,而是以“无碑、无像、无陪葬”三无著称。
学生来扫墓,只见麦苗青青,案台上插着纸鹤与一封封留言。有人写下:“愿我为人,也可如您,清白一生,土中无金。”
包拯临终布下七门疑阵,九百年后仍无一盗迹,不靠法度护墓,不靠天子守冢,靠的就是一句话:清官不死,心中长在。
发布于:福建省深富策略-智慧优配最新消息官网-正规股票配资机构-如何选择证券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
